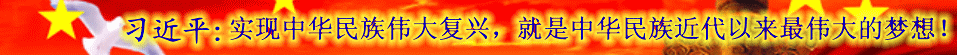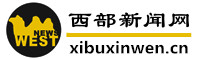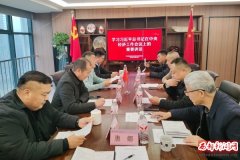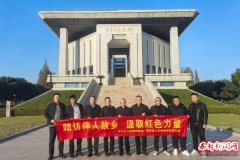当地政府已试图扶持这个被遗忘了的人群的贫困生活,但户籍,仍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这个庞大人群,禁锢于云南西南的偏僻山坳里。
也许,62岁的侯志强还得再“死”一次,这样他的八儿子便可以以“孤儿”的身份、花费较低成本拥有一个身份证并顺利结婚。
侯志强居住在开远市往西不到十公里的西山一个叫马头坡的村子里。――事实上,并不存在马头坡这个村庄。即使在当地最新版本的行政地图,它也被标记为荒芜的山坡,虽然这里住着117户人家,597人。
1980年,当侯志强和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来到开远城外西山上这块坡地时,这里还是飞鸟和走兽的领地,高大的树木和藤蔓植物遮天蔽日。他砍下竹木和藤条,割来田野里的茅草,搭建起勉强遮风挡雨的房屋,把家安在了这里。
之后的数十年里,坡上搬来了上百户人家,文山的、蒙自的,甚至还有贵州的人搬来。鸡犬之声相闻,村落渐渐有了规模,西山上茂密的树木消失了,成为房屋或者消失于炉灶。

明年小学毕业后,可能无法上中学,13岁的杨天勇泪流不止。

整个村子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了。由于没有自来水系统,村民的用水都必须从城里购买拉回坡上,一桶1.5元。
“老家那边土冷,长不出庄稼,不得吃嘞。”侯志强的老家就在开远市旁边的屏边县,当时的饥饿对他来说刻骨铭心。堂屋里,儿孙们掰完玉米休息了,他会佝偻着把灰土中洒落的玉米籽,一粒粒抠出来,放进口袋。他对故土并没有依恋,印象也仅停留在“山高土浅石头多”上,广种薄收。
侯志强到现在仍然在自己反复摩挲过的泥土中劳作。牛车里,新收的玉米颗粒饱满,丰腴的黄色如同马土坡的泥土一样。时间和劳作正在侵蚀着他的呼吸,一阵剧烈的咳嗽后,他的灰土面色如同牛车上装着玉米的旧竹筐,让人察觉到他经受一生的雨水。
侯志强和村民们是到后来才知道,大家居住的马土坡属于云南省开远市灵泉办事处三台铺行政村管辖。但他并不是这里的村民,准确来说,他们不属于任何行政单位,“也不能算作人民”。
他们被称作“黑村黑户”。在开远这个人口30万左右的县级市,像侯志强这样的“黑人黑户”登记的就有1300余户,总数超过6500人。他们分布在开远市8个山区村委会,共74个居住点。马头坡在侯志强等数十户人家迁入后,算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居住点。
这些“黑人黑户”在正式的文件中被称作“自发移民”。开远市自发移民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金学调查后发现,这一群体在遇到调查时“戒备心强,或者干脆躲起来”,真实人数估计超过1万人。
“我倒是没几年活头了,关键是孩子们活得没有盼头。”这些年,侯志强和村里的老人不再为找到一片可以吃饱饭的土地感到骄傲,相比于坡地上刀耕火种的劳作,为儿女身份问题的心焦,使得他们正迅速老去,而且他们所盼望的事情似乎毫无起色。没有户口,儿女们将无法考学、打工,也不能合法地结婚,即使男女组成家庭有了小孩,也只能是“黑二代”。
马头坡更像是一个孤岛,令侯志强的小儿子杨春华(侯志强随养父姓,儿子辈按风俗认祖归宗姓杨)常常感到孤独,周围村庄的年轻人去到广东打工,挣钱盖起了房子,而他却被困在这里动弹不得。
流浪“佃农”
侯志强怀念2001年农业税免除之前交7公斤“公粮”的日子, “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。”
家里耕种着近50亩土地,再也没有饿肚子的恐惧。这是侯志强脸上总有笑容的原因。
1959年,侯志强的养父因生计投靠住在开远市石洞村的妹妹,当时只有10岁的他也跟随养父来到开远。不久后,全家就加入了石洞的人民公社,参加公社的劳动,在食堂里吃饭。相比于之前生活过的屏边县来说,还是小孩子的他觉得开远好多了,“可以多吃一碗饭”。
歧视是在公社年尾分粮食的时候意识到的。侯志强发现自己只分得了“几捧玉米籽”,而跟他年纪相仿的当地社员却可以分得一蛇皮袋。他去找大队的干部才知道,当地青壮的男社员干一天活记“一个工”,而他由于是外来人员,只记“六分工”。
他想到这里毕竟不会太饿,就不再计较了。而且,大队里面有大会也会叫上他去参加,他觉得自己得到了接纳。结婚后,家里连续添了小孩,情况变得糟糕起来。1976年,侯志强一双儿女“抽筋”死了,因为营养不良的原因。
“三岁的儿子和三个月大的女儿,同一天死的。”说完老人顿了一下,喉骨陡然收紧,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。久远的悲伤被记忆捕捉,突然爬上密布皱纹的嘴角。
1977年,开远等地开始清查人口,侯志强和不少自发移民被强令搬回屏边居住。他不想走,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把他的茅草房扒开了。侯志强与9户人家结伴,背着大铁锅和碗筷回到了屏边,“那是全部的家当”。
在屏边住了三年,1980年实在生存不下的他又回到了开远。他说在路上吃野菜充饥,就是为了到开远。是年,他来到了马头坡,和陆续到来的人们在这山坡上生息。
当时,马头坡所在的三台铺已经“土地下户”了,侯志强这些新来者必须要租种当地农民的土地。“租一亩开始给户主30斤左右的玉米,后来就是给钱。”当时不少村民都自嘲是“交租子的佃户”,心里都忍不住地乐,他们还开垦了大量的荒山,村民间常为争土地吵得不可开交。马土坡进入了一个最为有生气的时间。
“时代毕竟在变啊!”这是马头坡老人们最爱感叹的一句话,山下的城市出现了工厂,人们透过远行的人了解到“广东”是一个极为繁华、遍地金钱的地方。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,原有的宁静平衡逐渐瓦解了。但马头坡人很快地发现,他们哪儿也去不了,他们去昆明想坐火车到外面,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作罢。
渐渐地,村民沮丧地发现他们住的村子也比邻近的地方“差远啦”,没有学校、没有公路、没有水窖、没有电、没有合作医疗、也没有种地的补贴,而周边的三台铺、德果、老邓耳、石岗等村庄都有了。惠农政策给这些有建制的村落带来了好处,诸多扶助还滋润到每一个农民的头上。
甚至村民有了余钱也不能存到信用合作社。前几年,村里一户人家的茅草房失火,烧掉了十数年积攒的数千元钱,看着一切化为乌有,一家人只能坐在一起嚎啕大哭。
马头坡被遗忘了,他们没有户口,没有“组织”。
在吃饱饭后,户口却扼住了马头坡村的咽喉。侯志强和其他父母们因为给子女“跑户口”,每年都要去好几趟户籍部门,但这么多年都是无功而返。他们不明白就是往电脑里“输一段号码”的事情,为什么就这么难?跑来跑去,这些老实的农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,后来户籍警总是跟他们说“你们也没户口,子女办不了”。
岁数上去了,侯志强心里空落落的,越来越怀念2001年农业税免除之前的日子。在那之前,村里每个人都要上交7公斤的“公粮”,每户还必须缴纳4元钱的“优待抚恤费”以及10元左右的“教育附加费”。政府的工作人员会收起这些钱款,并登记每户的缴纳额度。在当时,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仅有数百元,缴纳这些费用并不轻松。
“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。”老汉的语气中有些委屈。
没有年轮的村庄
现任“村长”是村里百余户家庭的户主用玉米籽“投票”产生的。
问到女儿的出生年月,眼前的李绍林想慌了神。46岁他的拥有9个孩子,他只记得女儿李美珍大约在10岁左右。
他住在侯志强家旁边,因为两家都有九个儿女,被村人看成是“多福”之家。但事实上,李绍林的家就只是一间低矮的石棉瓦房,墙壁是用竹子和木板编成的,目前他与妻子和六个2到13岁的孩子住在一起,“下雨就会飘到屋中”。
像李绍林这样记不住孩子出生年月的人很多,甚至很多年轻人都说不清自己是哪一年结婚的。老人们笑着说,记得那么清楚有什么用,只要记得“和村长的二娃娃是一年的”,就可以啦!
多数的家庭都没有电视机,村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会议,或者政策宣讲。在这个离开远城十五分钟路程的山村里,时间已经变得不再敏感。
甚至,马土坡上人家的墙壁也显得“干净”,没有标语,道路上也没有横幅。当然,村里有4户人家都还住在茅草房里,斑驳的泥土墙壁根本画不上油漆。由于是“黑人黑户”,无法管理,超生成为普遍现象,几乎家家的孩子都有四个以上。今年大旱,李绍林耕种的数十亩土地仅能收获4吨玉米,虽不用纳税,但交完租金,粮食也剩下不多,需要养活9个孩子的他也不知道明年怎么过。
“村里不能这么下去了!”有着初中文化的杨有林意识到如果没有教育的话,马头坡就彻底完蛋了。1991年,全村的村民用黄泥土筑起墙壁盖了一间房子作为村里的小学,杨有林就成了村里的第一个老师。侯志强把儿子杨春明送到了学校,他后来成为马头坡上的第一个中专生。
当时,马头坡村民借着帮助林业部门看护山林讲条件,由当地林业部门出钱购买学生的课本。而作为老师杨有林的酬劳则是不论家里有几个孩子,每户每年给他二十斤玉米和半斤煤油。第一届学生容纳了村里6岁到14岁的孩子,总计有五十多人,附近村庄不少“黑户”也把孩子送到了这里。
另一方面,村里关于土地纠纷也越来越多,村民想要选出一个“村长”方便调解矛盾,另外帮助村民争取“政策”。现任“村长”刘忠祥是2007年7月31日,村里百余户家庭的户主用玉米籽“投票“产生的。当时他获得的玉米籽最多,就成为了新一任“村长”。
刘忠祥说马头坡的“村长”都是“只管事,不收钱”的,他不接收上级村委会的薪水,也不从向村民收取辛苦费。在前任“村长”的争取下,2004年村里面通了电,但用电价却是每度0.55元,而一般农村用电每度仅0.402元,另外每户还得给村里电工每月1元的补贴。村民还自己动手修起了水塘。
但这种改变还是非常缓慢,村民们微薄的力量根本无法跟得上其他附近村庄的步伐。由于户口问题,杨有林发现绝大部分学生读完村小之后,就辍学回家了,上到初中的几乎没有,在任教8年后,村小解散了。由于没有自来水系统,村民目前的生活用水都必须从城里购买拉回坡上,一桶1.5元。
“村里要推广经济作物也会发种子给马头坡的住户,但效果不大。”三台铺村委会主任熊正义介绍说,村里也会尽量帮助这些“黑户”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,但在力量上仍然捉襟见肘。
2010年,马头坡所在的三台铺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400元左右,而马头坡村民中不少家庭的总收入还不足千元。
牛粪和草上面放着课本
村里女孩子十一二岁嫁人很平常。
现在的马头坡上,最漂亮的房子就属澳门慈善人士在2008年建立的道明小学了。这个小学只有一三四,三个年级,总计78名学生,没有户口的孩子超过三分之二。因为人数不足停招,二年级就缺失了。
在这所学校读书,家长不用缴纳任何学杂费,现在村里面的孩子都会在这里完成启蒙。学校两层小楼粉红色的墙体看起来温馨异常,而在楼下玩耍的孩子们多数却衣衫褴褛。李美珍13岁的哥哥李光亮已经从学校辍学回家放牛,她和两个弟弟目前仍然在学校里读书。
从建校开始就在村里任教的王海芬特别心疼李美珍,这个小女孩学习成绩不错,懂事勤劳。她每天下午回到家,还需要给四个弟弟烧火做饭,而且需要给村里面一个留守的老人做饭,获得很少的酬劳帮补家用。小美珍才9岁。
小美珍之前曾退学,王海芬到家里做了家访,她才又回到学校,虽然成绩很好,但在四年级辍学已成必然。她的两个姐姐已经在很小的年龄嫁人了,目前家里需要她照顾弟弟。王老师说,在村里女孩子十一二岁嫁人很平常,她教过一个叫刘芳梅的女孩子,四年级辍学回家不到半学期,就嫁到了外面的村庄。
“他们的父母没有认识到教育的重要,也没有那个能力。”王海芬痛心地说,就是家长有意愿学生们也最多读到初中。没有户口的孩子,无法参加中高考,也不能享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减免。这些年她在村里走访发现,马头坡村只有一个人读到了高中以上。
曾经是民办老师的杨有林,一直希望自己能把孩子送入大学,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学习成绩都很优异,孩子们的奖状都被他用塑料袋保存了起来,一层又一层。家里条件有限,五个孩子只能和牛住在一间屋子里。午后的光线穿过房顶的缝隙,照射出屋内悬浮的灰尘颗粒,扑鼻气味让人不能呼吸,孩子们的床就和牛的草窝一起,床沿前都是牛粪和草,上面整齐地放着一小叠课本。
上初中的大儿子会经常意识到自己是没有户口的孩子,感到不自在。有时候,谈到能不能继续上学的问题,父子只能围坐着默默地淌泪。对于未来,他不敢想象,“就怕孩子们恨我”。
缺乏教育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,刘忠祥介绍说2010年村里就有三个小青年在开远城里“抢钱”,被公安机关拘捕了。这些孩子几乎没有任何登记。
李绍林的儿子去到开远城里之后消失了,由于没有户口也没法报案,他只是听人说孩子被拐进了传销组织。遇到村里人打听他儿子的下落,他都会忽然噙着泪说“在桂林”。
“父母双亡”求户籍
父母生下了自己,而现在为了“证明”自己,却要说父母亲都死去了。
在侯志强的大家庭里,第七个儿子杨春明一直是家庭里的骄傲,他是马头坡第一个中专生。如今他在开远的一家企业工作,穿着洁白的衫和球鞋,干净清爽。27岁的他说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,就是想住在城里。
本来没有户口本,他不能参加中考,求学心急的他和父亲就只能去求户籍部门,开远警方给发放了一个暂住证。凭着这个证件号,他参加了2001年的中考,并以524分的成绩考取了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小学师资班(大专),他觉得自己的教师梦近在咫尺。
可是没有户口及身份证,学校根本不接纳他,侯志强带着他四处求告,没有效果。后来经过别人介绍,他去到昆明推拿职业学校读了中专,这里没有查他的身份证。毕业后,拿着中专学历证书的他胆气大了,直接去了公安局申诉户口问题,当时公安机关特批给了他一张身份证。
而他的哥哥们,却没有这样的好运了,每到结婚的年纪“家里都需要卖了牛和拖拉机”,才能缴清帮他们办理户口的“社会抚养费”。由于开远市不接纳,他们只能回到屏边县去办理身份证,而回到开远,他们仍然是异地居住的“黑人黑户”。
后来,户籍管理进一步严格,必须要出示父母的身份证明,才能办理子女的户口。2007年,杨春明的哥哥春云要结婚,拿着3000元回去屏边办户口。当户籍机关坚持要春云拿着父亲侯志强和母亲的身份证才能去办,这意味着办一张户口的成本将高达万元,就是搭上家庭全部积累也不够。在之前几个儿子结婚时,侯志强的家庭已经数次倾尽所有了。
杨春明灵机一动,春云可以谎称“父母双亡”的说法规避高额的“社会抚养费”,他让哥哥以自己的名字办理身份证,这样春云“结完婚不用身份证了”,他也可以拿着用了,因为他之前获得的身份证遗失了。
户口办了下来,全家欢庆,侯志强和老伴儿也很开心,家里省了好几千块钱。杨春明觉得心里堵得慌,父母生下了自己,而现在为了“证明”自己,却要说父母亲都死去了。
现在最让侯志强操心的就是老八杨春华了。这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,“上学没认识一个字”就回到了家里帮手农活,劳作的双手布满了皲裂的黑色细纹,沉默寡言的他几乎从不表达自己。
每天做完农活,他都会用洗衣粉将头发洗一次,梳理成中分的样子。然后,不动声息地换上城里买来的潮流,在衣柜镶着的镜子前照了又照,衣柜已经被熏得漆黑了。这是他一天最为休闲的时刻,坐在门前的土堆上,看着山下城中的路灯亮成一排排,霓虹闪烁。
他说自己曾到城里的网吧去过四次,因为没有身份证他没能上机去玩这里年轻人最爱的“劲舞”游戏。“朋友玩,我就站在边上看。”他语气中恍然有些失落。
在今年传统的花山节上,杨春华认识了一个18岁的开远姑娘,他害羞地说已经在谈婚论嫁了。这让年迈的侯志强觉得又喜又惧,能亲眼看到儿子们成家是他的福气,他并不忌讳“再死一次”。只是“上户口”需要的数千元费用,会让这个家再度回到贫困。
三台铺村委会主任熊正义也对辖区内这个马头坡感到头疼,虽然村委会无权管辖马头坡的住户,“但事情来了也分不清楚”。
2011年8月16日,开远市出台了一个自发移民管理实施方案,对他们提出一些扶持政策。“住户都来自周边各个县市,户口的问题在开远是解决不了的,需要省里或者红河州里做出安排。”常年帮村民跑户口问题的熊正义觉得“落户”太棘手了。(责任编辑:海洋)